《銹湖》(Rusty Lake)是由荷蘭阿姆斯特丹的銹湖游戲工作室製作並發布的恐怖風格解謎游戲系列,正作分為「銹湖」和「逃離方塊(Cube Escape)」兩個子系列。從2015年5月發布第一部解謎游戲《湖》(Cube Escape:Lake)到2023年9月27日發布新作《地鐵繁花》(Underground Blosom),該系列共推出17部作品——包括2020年4月重製的系列前傳《輪回的房間》(Samsara Room)——這些作品互相獨立又有機聯系,共同構成「銹湖宇宙」的宏大敘事。
作為一款恐怖風解謎游戲,「怪誕」是該系列的顯著特徵。玩家在交互流程中,可能遇到「熟悉的原材料構成最陌生的形象、最美善的東西構成最丑惡的對象、最現實的材料構成最超現實的東西」[1]。然而正如游戲名《Cube Escape》所展示的,「方塊(cube)」是游戲中給人印象最深刻的物象,也是《銹湖》獨具特色的一個設定。「方塊」作為被具象化的「記憶」,純粹、簡約、幾何化,在游戲的呈遞中本身是一種與舊澀復古的環境格格不入的超自然、超現實存在,也是標志性的怪誕的審美入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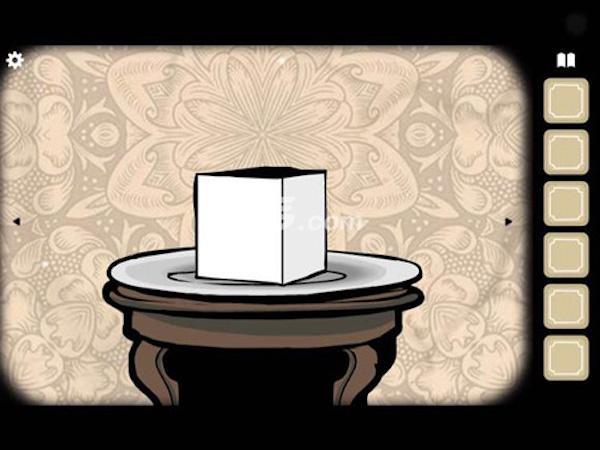
復古凱爾特風格布景中,超現實的方塊
1872年10月,維克多·雨果在為自己的劇本《克倫威爾》所作的序中給予了怪誕極高的評價。他認為,怪誕是一種新型的藝術,其特點是把丑惡引入藝術,使之與優美一樣,也成為藝術的表現對象。這種引入對於精神世界的影響是巨大的,「結合崇高優美而又不使它們相混」,「把陰影摻入光明」,「把肉體賦予靈魂,把獸性賦予靈智」。[2]

怪誕的審美入侵
無疑地,在這種假定下,將抽象的「記憶」作為具象化的主體具有特殊意義。將記憶具象化這一特殊設定,是將抽象概念實體化,可以看作是解謎游戲迎合玩家操作體驗的機制設計與流程載體,但從「記憶」主體本身不同於一般抽象概念的超驗與現實雙重屬性來看,以方塊討論記憶,本就具有了獨特的隱喻與探討的空間。這種獨有特徵也使得「記憶具象化」的游戲敘事方式帶有深刻的悖謬性。玩家在潛意識層面經歷陌視、懷疑與解構的三元認知後,被迫接受深層空間的設定。這一過程的實現是隱性而移覺的,也是深層空間富含隱喻與暗示的語境外化。
方塊的產生、流轉到終極的指向,都充滿了自反性的「悖謬」色彩。藉由方塊的隱喻,某種更深層次的話語構建成為可能。
一、方塊的誕生——福音式啟示與敵基督式崩壞
《銹湖》的故事被設定圍繞一個名為「Rusty Lake」的湖展開,時間維度跨越 18 世紀到 20 世紀共二百餘年。銹湖的「運作」既需要合理的水位,也需要新鮮的記憶方塊。記憶方塊是從人體內提取的。不同顏色的記憶方塊有不同的意義指向,黑色方塊代表痛苦的記憶,白色方塊代表美好的回憶,藍色方塊象徵穿越時間改變過往的能力,金色方塊則關乎通向未來的道路並與所謂的「長生不老藥」有直接關聯。被提取記憶的屍體容易腐化,變為具有仇殺屬性的「餓鬼」。而藉由記憶運轉的銹湖,具有多種神諭性的稟賦:接受獻祭、降臨啟示、賦予輪回、淨化靈魂。整個《銹湖》的深層故事,直觀上就是圍繞收集記憶、復活亡魂、解決餓鬼、尋求永生的邏輯展開的。
方塊的故事源起於《銹湖:天堂島》(Rusty Lake:Paradise),一段對「長生不老」啟示的追求。18 世紀,銹湖被詛咒,深居湖心天堂島的唯一居民 Eilander家族為了消災,決定獻祭長子Jacob,平息銹湖的憤怒。母親Caroline不忍,堅決用自己代替兒子受祭,並悄悄將Jacob送出天堂島。在被囚禁等待獻祭的日子裡,Caroline通過煉金方法研究出了長生不死之藥的配方。「One will die,the other will get enlightenment.(一人犧牲,一人得到啟示。)」這也成了圍繞整個銹湖故事的二元悖論。
母親被一家人綁起,活活燒死,產生了大量黑色方塊,母親也墮為餓鬼。
不過,銹湖的詛咒並未消除,十幾年後,父親、奶奶、叔叔、弟弟、妹妹以母親去世為由,將長子Jacob騙回天堂島,重新上演了獻祭儀式,其實也是為了獲得母親筆記里提及的「不死」啟示(enlightenment)。Jacob 通過收集母親留下的黑色方塊了解了一切,並在母親所化餓鬼的指引下,於最終的獻祭中得到啟示,成為半人半獸的不死之身貓頭鷹先生(Mr. Owl)。
天堂島的故事具有很強的聖經福音意味,化用的是《出埃及記》中的「十災」。在這里,「銹湖」扮演了一位降下天罰的神明,甚至是上帝的先驗存在,在此語境下,「獻祭與拯救」「懺悔與啟示」本應是理所當然的,但「記憶方塊」的出現打破了這一自然邏輯,賦予所謂的基督式「啟示」以敵基督的反叛意味。
「十災」的降臨,本是神為了懲戒法老的罪孽而布下的警告,而在天堂島,所謂的「原罪」是何無從宣告。在銹湖這樣一個風景優美與世隔絕的環境中,人的道德也許本應如梭羅的瓦爾登湖般純粹、原始與良朴,然而湖的本性卻呈現崇高與黑暗的分裂,人的本能也呈現追求私利甚至泯滅親情的惡,難以判斷是人的惡招致湖的罰,還是湖的罰腐化人的惡。前置的條件被淡化,最終降臨啟示的主體也就變得可疑。

家族的獻祭與黑色方塊
在這種語境下,「記憶」以方塊的形式第一次出現。記憶象徵着本體的內在自我空間,這是對抗外在至高存在的唯一可能。從游戲的第一人稱視角帶來威脅與恐懼感的,最直接的往往是失去記憶後的餓鬼,但這種錯置容易使人淡忘背後面對的更加龐大的「無物之陣」——銹湖。
在奧古斯丁的聖經解釋學理論中,「愛」被置於先導和核心地位。在論述有理性的人的靈魂結構時,奧古斯丁將其描述為「記憶、理解和愛」的三位一體。[3]在這里,記憶是靈魂對所在對象的記憶,理解是靈魂對於所在對象的認識,而愛是靈魂與所愛對象最本質的關系。
這也是《聖經》教義下「愛上帝與愛鄰人如同愛自己」的解釋性原則。不過,身體力行「道成肉身」以尋求啟示的精神性追求與道德價值體系,在銹湖實現了恐厄與貪念交織的敵基督式崩壞。正如尼采指出,耶穌受難後,以使徒保羅為代表的教士階層為攫取民眾統治權,利用怨念、內疚心理將耶穌聖化為上帝派來為人類贖罪的「彌賽亞」,製造出原罪、復活、重臨、審判等教義,由此傳播福音,寬恕敵人、無意世俗權力、作為兄弟姐妹的耶穌,被顛倒成散布「厄音」、要求懺悔、賦予教會權力、作為父親形象的基督。[4]在Eilander家族的獻祭中,我們看到的正是這樣一個毀惡、愚詐的至高力量的代行者。
記憶方塊的存在,是Caroline為家族犧牲的實體化見證與遺存,也是對血罪最原初的揭露,其承載的,也就是以個人之靈魂反叛絕對性的先驗力量的真正「啟示」。
《銹湖》游戲中,還多次出現對宗教油畫的改畫,如多次出現的油畫《Lady of the Lake》,是對《莎樂美與聖施洗約翰的頭顱》的改畫,畫中女子所端的盤子上盛放的本是約翰的頭顱,被改為黑色的方塊;相似地,《對無辜者的殺戮》中,畫面中央本是殘暴的希律王,也被改為黑色的方塊。方塊的存在,是一種幾何化的諷刺,也是夸張化的反叛。

《Lady of the Lake》
尼采高呼「上帝已死」,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對以盲信、怨恨、殉教為基礎建立的救世主精神進行批判,與之類似,通過以真正的愛構建的記憶,Caroline 得以成為真正能夠帶來解救的偉大者,即「超人」。也許這也是她的肉身雖墮入餓鬼,仍保持着為兒子指引方向的清醒的原因。
在「新基督」的理論下,德勒茲將真正的耶穌闡釋為一種世俗的生活方式和感受方式,而非基於審判教義的信仰體系。[5]「新基督」的內涵是尊重人的生命主體與「超善惡」的倫理觀。這種討論意義下,方塊的誕生,無疑是對偽善舊式福音的無聲控訴與新基督的象徵性回應。向神學尺度的哲學提問,為方塊的進一步探討埋下伏筆。
二、方塊的流轉——內向性的輪回與外向性的救贖
《銹湖》世界觀中另一重要設定是佛教中的「六道輪回」。這是佛教中最基本的世界觀,認為一切眾生因因緣業力不同,將生死流轉於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六道中,佛教修行的目的是消滅業障而擺脫輪回、出離生死。
《銹湖》在這一前提下的設定也是表面自洽的,如 Jacob 得到啟示進入阿修羅道成為貓頭鷹先生,Adous 服用長生不老藥進入阿修羅道成為烏鴉先生,被提取記憶的屍體腐化墮入餓鬼道等等,《銹湖》中幾乎所有角色,都可以在六道輪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六道輪回與「啟示」
然而「記憶方塊」的存在使得「輪回」本身的意涵不再單純。將「記憶」物化,意味着賦予了其轉移、存儲、使用等工具屬性,由此帶來的是「輪回」邏輯的重構。在通常的六道輪回理論中,生前積累了過多惡緣業障,才會墮入惡道,而在銹湖,被提取記憶的屍體發生腐化,墮入餓鬼之道,這與記憶者生前的善惡因緣是無必然關聯的。同時,進入阿修羅道長生不死之境,似乎總要伴隨犧牲。貓頭鷹先生是因為得到了母親長生的啟示,毋寧說是因為母親的犧牲;烏鴉先生與其兄長William Vanderboom先後飲下長生不死藥,烏鴉獲得了長生,而William則瞬間死亡,成為餓鬼。William的轉世重生,需要Vanderboom家族10名成員分別獻祭一個身體部位以及「時間碎片」(可以看成記憶的另一種物化形式)完成犧牲。
可以認為,「輪回」在銹湖世界中不僅僅是作為世界觀設定而存在,更是一種方法論。它指向的也不是作為客體的外向規律,而是作為主體的內向生命存在狀態。向外追尋,每一個個體都渴望突破限制,達成某種決定的意志;向內窺探,每一個個體又在自我決定與客在決定的歧路搖擺不定。
另一方面,許多玩家傾向於將《銹湖》的風格描述成《百年孤獨》式的宿命感。事實上,百年孤獨的滄桑與悲涼,正來自於布恩迪迦家族每一個成員內向性的追求被集中於線性單向而又封閉的時間中,產生的孤獨索跡。而在《銹湖》中,具象化的記憶將主體內向化的追求公之於眾,記憶不再是主體的私藏品,藉由「物體化」、「工具化」的方塊,記憶被剝離了抽象的所有權,通過他人之手的改變、隱藏、發掘,由此為內向化的輪回提供了一種外向化的出口——救贖。
Dale偵探通過銹湖的電梯在記憶的時間中旅行,通過藍色方塊修改童年的痛苦回憶,將黑色方塊變為白色方塊,William的魂靈在輪回的房間進行自我的舍棄與抉擇,實現轉生,這是自我的救贖;Laura在記憶的輪回中改變過往,讓改變隨時間發芽,這是意念的救贖;Dale在悖論的房間無限輪回,最終選擇犧牲自己淨化Laura,拯救銹湖,Sarah刪除Bob關於Laura的記憶,這是他人的救贖;年輕與年老的Rose通過時光機器合作獲得金色方塊,復活Albert,這是時間的救贖。
《銹湖》中有一句台詞 :「Every you touched,you changed.(你所接觸的一切皆因你而改變。)」,便是外向性救贖的體現。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呈現了成熟的「永恆輪回」時間美學,其體現的是對「大地性」的回歸與對「身體感」的重視,本質是主體內在的強力意志。
「Balance the substance of your life.(平衡你生命中的物質。)」是游戲中需要通過調節物品重量達成平衡以通關的常用提示語,也是關乎生命主體面對宿命的能動性的隱喻。
生命可能逝去,但願望不會;靈魂可能腐化,但愛不會;回憶可能消散,但意念不會。藉由「記憶」的超時空屬性,《銹湖》突破了《百年孤獨》式的線性時間,在輪回與救贖的相互博弈中走向時間的閉環。
三、方塊的旨歸——過往未來:改變與逃離
重新審視「方塊」在游戲中的設定,它誕生於接受福音式的先驗啟示,卻指向反叛厄音式的道成肉身;寄託圍繞本體的輪回,但卻指向賦予客體身體性的救贖。在討論這些本徵性的悖謬同時,方塊作為「記憶」,其本身作為跨越時間工具的使命本身的背景並未消失。
「記憶方塊」帶來的最深刻的悖謬,正是關乎時間的討論。
「Past is never dead, it is not even past.(過去從未消亡,它甚至從未過去。)」「Memory is not only key to the past, but also key to the future.(記憶既是通往過去的鑰匙,也是通往未來的鑰匙。)」是《銹湖》中關於記憶與時間關系最直接的表述。在這一層面,記憶是連接現在與過去的關鍵,記憶可以通過改變現在而改變過去,也可以通過修改過去影響現在。
「銹湖」在引導每一位見證者用時間輪回的視角理解湖與記憶。
然而,《Past Within》中,當過去的年輕Rose與未來的年老 Rose手中的金色方塊通過時間機器重合,Albert得到重生,結尾的字幕顯示:「循環已經打破,裂縫已經閉合。銹湖不再擁有時間,過去與未來融為一體。」至此,銹湖關於過去、未來、現世輪回的一切敘述,都指向了時間結構的自反性崩塌。這種崩塌不是對所有拯救性改變與嘗試的消極否定,而是另一維度上基於人之認知主體性的重構。
時間的終極意義源自永恆。在《蒂邁歐篇》中,柏拉圖認為宇宙的原型是一個無開端也無終結的真正意義上的永恆生物,而「時間」則是其依數運行的影像。這作為永恆之影像的時間可以被視為一個由不斷生成的時間部分拼湊起來的無限。在這一無限中,可以獲得兩個時間概念,其一是作為單個時間存在的現在;其二則是由無數個現在連綴而成的時間之總體。這一時間的總體性存在是依據永恆為其理想性質的,因而也可被視為永恆性的存在。
特別地,立足於對「過去」和「將來」兩種時間概念的解釋,柏拉圖給出了區分以上兩種永恆的可能性與合理性。一般認為過去和將來是時間的構成部分。但過去和將來都被柏拉圖稱為「時間的生成方式」。在他看來,過去、將來與現在不是同等地位的概念,現在就是時間本身。現在依過去和將來兩種生成方式展開的運動並非周而復始和一成不變,而是不斷變化的。時間的生成意味着時間能夠產生出不同於自己的部分,因此我們才能說事物存在於不同的時間(現在)之中。而過去、將來這兩個概念則是用來區分不同時間之關系的。每一個時間都處在和它之前的時間的過去相續性,以及和它之後產生的時間的未來相續性這兩種關系之中。柏拉圖認為,原本的永恆不存在過去和將來,人們常常錯誤地用過去和將來這兩種時間生成方式,來理解作為原型的永恆,因此必須作出一個兩種永恆的區分:作為原型的永恆不運動、不變化、固守於一;而時間連續性之永恆則是生成變化的無限延續。[6]
柏拉圖對兩種永恆的區分也宣告着兩種基本時間視域的產生:一個是神學視域——原本的永恆作為時間主體存在;一個是哲學時間視域——時間總體性的綿延作為時間現在成像。
在《銹湖》的語境下,以輪回為前提探討的連續性永恆一直存在,這是哲學性的;而當記憶凝成的金色方塊使得過去與未來互相包含,這就返璞歸真式地使得本體性永恆進入世界的背景,這是神學性的。
通常認為,貓頭鷹先生為代表的銹湖「執政者」,追求的是真正的長生不老,即「天道」的奧秘。然而事實上,通過《逃離方塊:悖論(Paradox)》中的相關細節可以發現,貓頭鷹先生是知道自己下一道的輪回是隨機的,很可能落入畜生道,他也在積極地將 Dale培養成自己的下一任接班人,去接觸,去發現,去拯救,去犧牲,以期「銹湖的光輝之日再度來臨」。
在神學性永恆時間下,一種新的解讀成為可能:銹湖所有生靈的踽踽獨行、蹣跚跬步,都是在充滿悖謬但無限延長的時間閉環中對「啟示」的追尋。在這里,「啟示」已不再是長生不老等內在的訴求指向,而是客觀的、形而上的「絕對真理」。就像《2001:太空漫遊》中「黑石」所象徵的文明的絕對崇高與啟示,在銹湖,「記憶」的最終具象最接近朝聖者本體,也最接近「過往未來(Past Within)」的真理本身。

《2001:太空漫遊》中的「黑石」
至此,筆者嘗試回答一個問題:記憶方塊作為系列經常要收集的重要物象,為什麼要將子系列命名為「逃離方塊(Cube Escape)」呢?
淺層來說,「逃離」是解謎游戲的標志;深層來講,「方塊」是記憶,也象徵過去、現在與未來,「逃離」也許是一種對往昔的救贖,對現世的反叛,對未來的抉擇。逃離己身現有的一切時間觀念、輪回世界,踏上一條劍指宿命的、「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殉道式的[7]啟示之路。
四、畫外之音——異托邦與時流狂想
瑪麗-勞爾·瑞恩在《故事的變身》中談到:「任何基於語言的虛構敘事至少涉及兩個層次:一是現實世界層次,作者同讀者交流,二是一級虛構層次,敘述者同受敘者在想象世界裡交流。每當一則敘事生成另一則敘事,就像敘事堆棧增添了又一個層次。」[8]
經歷近十年的發展,《銹湖》系列的敘事也不再限於游戲本身。當「記憶方塊」的魅影滲出屏幕之外,虛擬與現實的邊界被模糊,「真相外空間」的敘事得以構建。在這里,記憶方塊所有對於時間的討論在現實中得到了映射。
在《白門》(The White Door)、《過往之間》(The Past Within)、《地鐵繁花》(The Underground Blossom)發布之際,官方都舉辦了大型 ARG(Alternate Reality Gaming,平行實境游戲)活動。活動橫跨十數國家,雖由官方發起,但毫無預告,毫無規則通知,完全由玩家自行進行。細心玩家從官方發布的奇怪直播或是游戲中的莫名彩蛋中發現線索,通過解密音頻、查源代碼、登錄虛構網站、接打虛構電話等多種腦洞大開的方式步步探索,獲得個人專屬線索,最後由全球玩家通力合作將線索匯集,在線下尋找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游戲中物品(黑方塊),最終完成解謎,實現對游戲劇情的改寫,或是隱藏成就、紀念彩蛋等的獲得。

《銹湖》ARG
福柯提出的「異托邦」概念或許可以在某些意義上提供觀察記憶方塊「越界」的視角。
作為福柯空間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異托邦」是中斷了日常時空經驗的異在空間,卻是真實的存在。作為「反場所」,異托邦的異質性被保留,以非均質、非線性的時間秩序、非同質的空間結構,對日常生活的同質空間進行着批判與補償。
福柯用「鏡子」比喻異托邦,其可見性並非由實體呈現,而是通過鏡像空間對實體的映射展現。
在此鏡面中,我看到了不存在於其中的自我,處在那打開表層的、不真實的虛像空間中;我就在那兒,那兒卻又非我之所在,是一種讓我看見自己的能力,使我能在自己缺席之處,看見自身。[9]
如果我們承認《銹湖》通過線上線下平行解謎的方式構建了一個以方塊為載體的「異托邦」,那麼,這一面異化世界的「鏡子」,其反照的又是實體世界的什麼呢?
人們熱衷於參與《銹湖》的線下解謎,在實體世界中尋找記憶方塊,主觀能動地容身於銹湖的世界觀中,這或許寄予的是後現代社會的人們的某種時流狂想。
人類的田園牧歌早已結束,高歌猛進的自信躍進也已不再。高競爭、高內耗成為社會症結,暗流與沖突從未遠遁,全球難題接踵而至。尤其是後疫情時代,人類社會的精神面貌發生進一步改觀。經歷過犧牲,才知道生命可貴;經歷過苦難,方顯得和平可歌。如果能有時間回溯的手段,如果擁有修改過往的能力,每個人都希望與過去的自己和解,與未來的自己留下珍重的諾言,每個人都希望留下愛與美好,每個人都希望珍藏自己的唯一。
即使無法實現,也應在現世的幻想中有過一次狂歡,至少,透過「記憶方塊」隱喻的門,我們得以回望曾經的流金歲月,至少,我們曾經美好過。
五、余論
《銹湖》是一部無解的書,每個人都可以從中擷取自己的吉光片羽,讀出自己的心靈感觸。「記憶具象化」是一種獨特的游戲敘事設計,限於筆者水平,本文僅代表一種個人化的解讀。希望此文拋磚引玉,引起更多對類似游戲的關注與研究。作為「第九藝術」的游戲,其文化價值不應被忽視。
總而言之,「記憶方塊」所記錄的丑與惡,滑稽與恐怖,是伴隨着美好、崇高一同客觀存在着的。怪誕的意義不在丑惡本身,而在於丑惡的揭示與昭告;生命的長度里不會缺少丑惡,但丑惡可以沉澱生命的厚度與深度。經歷過苦痛,依然珍惜回憶,依然嚮往美好,依然跌爬滾打。活在當下,熱烈而自由,亦如平凡大地上前行的芸芸眾生。
(本文為清華大學「寫作與溝通」課程「游戲與文化」主題課堂學生結課文章,原標題為:方塊的隱喻——《銹湖》中「記憶具象化」的深層話語構建,參考資料從略)
注釋:
[1] 劉法民:《怪誕:美的現代擴張》,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0年,86-88頁。
[2] 【法】維克多·雨果:《雨果論文學》,柳鳴九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 年版,30-31頁,33頁,35頁。
[3] 張帥:《奧古斯丁的聖經解釋學研究——以愛為原則的闡釋》,博士專業學位論文,武漢大學哲學院,2019 年,53頁。
[4] 石繪:《內在性的「道成肉身」:論德勒茲「新基督」的譜系和意涵》,《文藝理論研究》,2022年第1期。
[5] 石繪:《內在性的「道成肉身」:論德勒茲「新基督」的譜系和意涵》,《文藝理論研究》,2022年第1期。
[6] 楊潔高,孫尚誠:《宗教時間與哲學時間:從柏拉圖宇宙生命論到舍勒現象學神學》,《昭通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83-87頁。
[7] 《論語·里仁》中的「朝聞道,夕死可矣」,談及道與生死的關系,由此引申出人身與價值的討論。歷代注家對此「道」的解釋,大體上可以分為禮樂文明的政治理想、順隨宇宙的大化流行以及道德主體自我實現三種。此處的引用,借用的是其對個人及世界存在價值構建的形而上學語境。參見陳德明:《儒家死生之道的形而上學構建——基於「朝聞道,夕死可矣」的三重解釋進路》,《江西社會科學》,2022年08期。
[8] 【美】瑪麗-勞爾·瑞恩:《故事的變身》,張新軍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287頁。
[9]【法】米歇爾·福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陳志梧譯,包亞明主編:《後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頁。